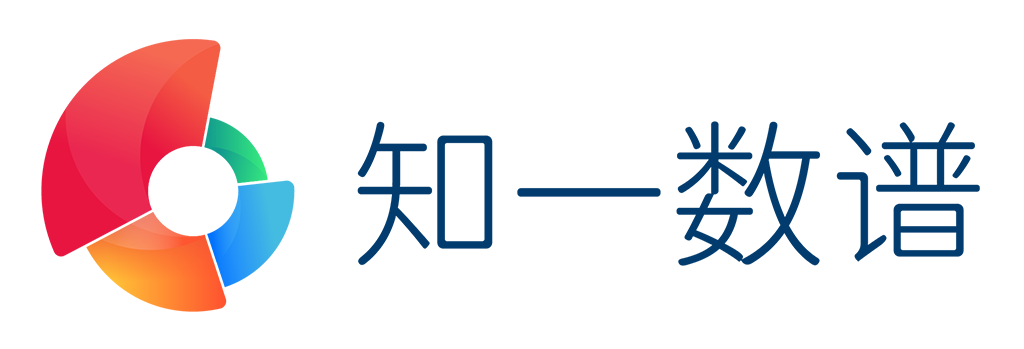不平等与鸿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原创 杨军 知一思享
2025年10月08日 08:08 湖南
在9月19日由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纽约办公室(UNITAR-NYO)和知一产业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产业学:全球协作下的产业重构”论坛暨产业学研究成果发布会上,Amaj Midani先生主持了专题研讨环节。期间,非洲数据科学领域的标杆机构Zindi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elina Lee女士,说明了非洲面对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通过培训和技术对接,链接全球人才与非洲本土需求所做的种种努力,并强调:随着AI浪潮的来临,以非洲为代表的发展中地区和国家必须直面接踵而来的AI鸿沟!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研究分析师Antonio Gonzales先生谈到,《人类发展报告》2010年引入不平等调整人类发展指数(IHDI),以便量化“不平等”对发展成果的侵蚀后,全球的IHDI曲线一直在稳步下降,直至2022年后开始掉头向上。UNDP将这一趋势变化——全球正在变得更加不平等——归因为全球供应链重构叠加AI技术冲击的结果。
对于科技重塑社会的关注可以追溯到1934年,科技哲学与城市史学家Lewis Mumford在《技术与文明》中认为技术发展都伴随着权力集中和社会分化。1990年,美国未来学家Alvin Toffler在《Powershift》一书中,首次提出“信息富人”(Information Haves)与“信息穷人”(Information Have-nots)的对立,并使用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一词描述信息技术引发的全球分化。
对人类不平等的讨论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就开始了。
法国哲学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中提出,原始社会的人类因资源共享而平等,但随着私有制出现,财富和权力逐渐集中,导致阶级分化。到了二十世纪,基尼系数,Simon Kuznets提出收入不平等随经济发展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假说,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与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OPHI)合作发布的多维贫困指数(MPI),使得对不平等的评估得以量化。
纵观历史,新技术出现后,最先被少数个人、群体或国家所掌握,催生分化或鸿沟的形成,必然加剧社群、国家乃至全球的不平等。在人类历史中,这样的故事至少上演过七次。
卢梭曾说过,12000年前以采集和狩猎为主流谋生形态的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平等的时代!新石器时代,人类驯化植物发展了农业,驯化动物后有了畜牧业。农业允许人类定居,形成了村庄和城镇,并生产出剩余粮食。这导致了财富的积累和私有财产观念的出现,为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奠定了基础。定居的农业社会能养活更多人口,发展出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如国家、军队),从而在军事上对分散的狩猎——采集部落形成压倒性优势,导致后者的土地被侵占、文化被同化或消灭。与家畜的接触孕育了天花、麻疹等新传染病,这些疾病对没有免疫力的其他人群(如美洲原住民)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有产者和无产者、定居者与采集狩猎者之间的鸿沟,至今仍然在土地契约、国家边界、环保理念等领域体现影响。
5000年前出现了文字和书写技术,法律、行政、科学和文学得以发展,官僚系统和大型帝国治理成为可能。但由于羊皮纸、竹简等书写材料成本高昂,文字和知识被祭司、官吏等精英垄断,极少数家族掌握知识传播和社会决策,并不断夯实统治和贵族阶层的根基。无论中国、中东还是欧洲,普通民众都是文盲,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知识体系和政治决策之外。在全球各个国家,消弭知识精英与文盲大众的社会割裂,都是伴随工业化进程得以实现的。具体到法国、俄罗斯、中国、巴西和印度,识字率突破80%的时间分别是1900年、1937年、1995年、2000年和2023年。
十五世纪开启的大航海时代,造船、罗盘、天文导航赋能的远洋航海技术,与火炮等军工技术结合,将世界各孤立的文明区域真正连为一体,也开启了全球性的殖民。
欧洲国家建立了全球殖民帝国,系统性地从美洲、非洲和亚洲掠夺贵金属、原材料和农产品,导致至少5000万原住民的死亡,还将数千万非洲人贩卖到美洲种植园。旧大陆与新大陆、殖民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鸿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制度化的不平等。这一时期确立的欧洲为中心、亚非拉为边缘的早期全球经济分工,其惯性影响持续至今。
十八、十九世纪,蒸汽机技术取代了人力、畜力和水力,英国借助机械化纺织和铁路开启了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后,带动整个欧洲最早步入工业时代。彼时的非洲、南美、亚洲仍100%依赖手工劳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美墨战争,英缅战争、英国征服苏丹的马赫迪战争,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都是工业国热武器对非工业国冷兵器的降维碾压,战损比达到了1:100,甚至1:1000。全球经济格局分化为工业国与原料供应国,工业化的国家内形成了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
十九世界末二十世纪初,电力、内燃机和化学工业的诞生共同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德国、美国等后发工业国在快速发展后与老牌殖民国英、法、荷矛盾加剧,事实上激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产业从纺织、食品等轻工业过渡到钢铁、机械、造船、化工等重工业,制造效率和运输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战争形态也被重塑。技术差距的累积,首先强化了全球殖民体系,其次使得技术垄断国与技术依附国,以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鸿沟得以形成,并且开启了全球资本流动,固化了中心剥削边缘国际分工和经济格局,成为今天全球贫富差距和气候危机的历史根源。
二十世纪上半叶,石油和天然气取代煤炭成为能源的主要来源,内燃机和流水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也带来了新的分化。拥有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的后发国家,很多陷入了政治腐败、经济结构单一的资源陷阱。工业化国家将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享受了发展的成果,却让后者承担了更多的环境代价,造成了新形式的不平等。全球经济分工固化,工业化的核心国家与非工业化的边缘国家之间“原材料-制成品”鸿沟逐渐固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发展,信息获取和传播方式被颠覆,催生了平台经济和大量新业态。信息终端和接入基础设施早期的高昂价格,事实上造成了使用技能和收益上的巨大差距,将数字鸿沟、算法鸿沟带入人类社会。赢家通吃成就了超级平台企业,基于数据和智能的新型不平等、叠加算法歧视,正在急剧扩大全球和个人间的贫富差距。
技术鸿沟或者技术分化,在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且其本质与新技术扩散的不均衡性和社会资源分配的结构性矛盾密切相关。
正在扑面而来的AI及算力革命,可能也会引发智能鸿沟。这将不再是简单有无访问权的不平等,而是智能拥有者——智能依赖者——智能边缘者之间的裂隙,也许会催生能力、机会和主权层面的根本性分化。很多劳动力市场会被部分替代甚至颠覆,知识型和白领工作被AI替代可能诱发中产阶级空洞化,进一步拉大资本与劳动的回报率失衡。AI可能会催生比亚马逊和谷歌更庞大的公司,当AI技术和生态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政府的监管和立法速度时,“公司主权”可能需要被直面,甚至挑战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而可控核聚变一旦成功,会带来类历史上最极端的有源与无源的分化,以及更震撼的能量鸿沟。能源可以用极低的价格,接近无限获取,粮食可以彻底摆脱耕地限制,建材、冶金、化工等能源占比很高的的产业必然被重构,海水可以无限淡化,大规模太空开发成为可能,现有能源体系,与能源体系捆绑的货币体系都将被颠覆。
此外,脑机接口与神经技术也许会带来生物认知鸿沟,基因编辑与合成生物学可能引发基因鸿沟,量子计算未必不能诱发密码与模拟鸿沟。
面对技术迭代与不平等演进的历史循环,人类总会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
AI与可控核聚变等技术的颠覆性潜力,既可能重现“智能垄断”与“能源霸权”的新鸿沟,也可能成为弥合旧有分歧的契机。技术本身无涉善恶,但其应用必然承载价值选择。若放任市场与权力逻辑主导创新扩散,则鸿沟必将深化。
唯有以全球协作与包容性治理为基石,将公平正义嵌入技术发展轨迹,才能使创新红利惠及全人类。未来能否打破“革命-分化-不平等”的宿命,取决于我们今日能否以史为鉴,主动构建一个技术普惠、命运与共的新范式。
知一思享
何志毅教授领衔的产业研究的成果展示!外部产业研究的优秀成果采集!何门师生的思想精华荟萃!
211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作者 杨军
知一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责编 草堂月 | 美编 邹邹